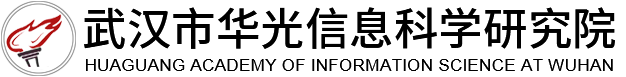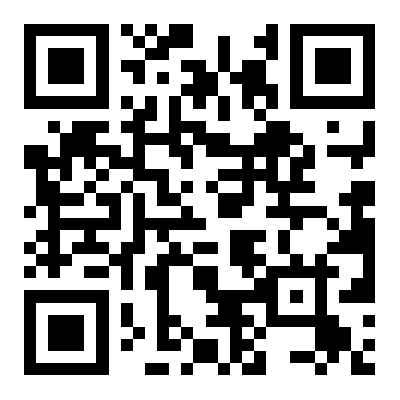网站首页 >> 2025 SIS 展示 >> 田爱景,李宗荣:批评斯大林哲学的错误,为
2025 SIS 展示
田爱景,李宗荣:批评斯大林哲学的错误,为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奠基
批评斯大林哲学的错误,为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奠基
田爱景1,2,李宗荣1,2
1 武汉市华光信息科学研究院
2 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摘 要:在结束国内外“只有信息技术,没有信息科学”局面的当下,必须破除“物质一元论”和它的同伴“信息虚在论”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不良影响。事实上,过去辩证唯物主义被冠名为“主流意识形态”,哲学家与科学家都必须宣布自己的“立场”是唯物主义。信息社会的到来,人工智能的火爆,学者和公众都认识到,世界是“物质-信息”二元的,不是“物质一元论”的。为了在哲学和科学上拨乱反正,现在必须批评斯大林哲学的错误,肃清斯大林哲学的流毒;必须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即“马克思哲学”。
关键字:斯大林哲学,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信息哲学,信息科学
 第一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简介
田爱景,女,河南省濮阳市人;1946年9月生;武汉市华光信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 员;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79年在武汉 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进修;先后在武汉大学与湖北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007年于湖北 大学退休。主要研究领域:信息科学、计算机软件。代表作品:论文,试论泛计算主义与计 算信息 学、On the Information Complexity of a System ;著作,社会信息科学导论》、 《Visual ForxPro 6.0 及其程序设计。
1. 什么是“斯大林哲学”?
简言之,所谓“斯大林哲学”,就是斯大林1938年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58年编写、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上下册),就是艾思奇1961年编写、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教材。斯大林哲学,在苏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就结束了,但是在中国却能够延续至今。它的“变体”是各种不断改变的、占据中国大学讲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即“教科书哲学”。它就是中国大学生们都阅读过、讨论过,通过课程考试、获得成绩的那个“哲学”。
这样,“斯大林哲学”肯定地与1961年以来的每一个中国大学毕业生有关系,一直是各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基础。
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由党中央决定实施,总体规划了139种高校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教材,由教育部和中宣部组织编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框架性认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1年以前曾经接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从1841年下半年起转向 L.A.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们吸取G.W.F.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摈弃其唯心主义,吸取费尔巴哈哲学中唯物主义而摈弃其形而上学和社会历史问题上的唯心观点,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创立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这不就是我们曾经背诵得滚瓜烂熟的几句话吗?与我们1964年入学的武汉大学数学系6932班学习的哲学教科书(“教科书哲学”),完全一致。这,就是“斯大林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为什么说,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哲学,就是“斯大林哲学”呢?
首先,马克思的全部文稿中没有称他自己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是历史科学(以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不包含辩证唯物主义。
其次,恩格斯曾经称自己的哲学是“唯物辩证法”,但从来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的称谓。
请注意,“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与“辩证的唯物主义”,两个“术语”都是“复合词”,具有组词意义上的“偏正结构”。但是,前者的核心词是“辩证法”,后者的核心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关于“对立统一”现象的学说,比如“物质”与“信息”对立统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统一。宇宙万物都是由物质和信息构成的。所以,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都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去认识“对立统一”规律,于是就形成了两种“辩证法”的理论。比如物理学的“正电与负电”,信息学的“正确与错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典型的“唯物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典型的“唯心辩证法”(或者“观念的辩证法”)。
但是,在“辩证的唯物主义”一词中,“辩证的”与“唯物主义的”,两者的基本属性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辩证”是“二元论”,而“唯物”是“一元论”;说“二元论的一元论”,在逻辑学上,就等于说“圆的方”、“方的圆”,显然不对。
第三,不仅李宗荣、田爱景等考证、论述“教科书哲学”是斯大林哲学(见《今日要闻》第75期附件),而且“马工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见原著第295页),日本学者(见《今日要闻》第76期附件)也这样主张并且给出论证。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百度”一下,容易查到原文)称马克思主义包含: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他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唯物史观”,完全没有说“辩证唯物主义”。
第四,斯大林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今日要闻》第75期附件中有论述,这里不予赘述。
2. “斯大林哲学”对于我们的误导
1938年,斯大林写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以及用单行本发行。1958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再次出版。1959年,中国翻译出版该教材。1961年,学者艾思奇参照苏联教材,撰写、出版《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大学马哲教材。到2025年,中国大学生被斯大林教材误导了半个多世纪了!
马克思在世的时候,虽然有撰写、出版自己哲学著作的计划,但是没有实现。马克思连他自己的《资本论》在生前都没有完成。在马克思看来,他的“历史学”和“经济学”都是“实证科学”,不是哲学。马克思心目中的“哲学”,是既“解释”世界,又“改变”世界的学说。为了改变世界,不仅仅是“批判”世界上的旧制度,而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旧制度。因为千百次的批判,毫无用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还要靠物质的力量来摧毁。”那么,谁来摧毁?当然是无产阶级。“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如何掌握群众,群众如何革命呢?马克思指出,哲学必须研究“意识的”、“主观的”、“能动的”主体,研究通过人的感性活动,通过“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才能摧毁旧政权。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斯大林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批评的这种“旧唯物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张的“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哲学的过程中,他必须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他根本没有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选边站”。但是,斯大林哲学与马克思哲学截然相反,它坚决地主张: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而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的世界观。至于“二元论”,那更加离谱,当然也属于被批判、被革命、被打倒之列。
事实上,在计算机系统中,不是“软件”比“硬件”更值钱吗?某个单位引进一个“海归博士”,不是引进他的思想与学问,而是引进他那100多斤骨骼与肌肉吗?李宗荣1994年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哲学系听课,发现他的老师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没有“唯心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在那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美国!)“大行其道”!李宗荣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博士后老师,阿根廷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中国的“院士”),移民到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101岁时过世;这位M.A.邦格教授,公开地主张与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推出他的“系统唯物主义”新产品。他称得上是反对“唯心主义”最为坚定的“革命党”的模范党员,请到中国来可以评他为“最美社科人”。
把哲学研究、科学研究直接与“政治站位”挂钩,直接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仅错误,而且是荒唐,更是愚昧、无能!苏联的李森科事件,非常典型。它作为经历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苏联科学史上的一场灾难,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长期停滞的末路。其始作俑者李森科本来学识浅薄、无甚建树,却荣居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他以“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的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三四十年。在1930-1960年间,苏联科技史上的这个“李森科事件”,实质上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引自“百度”网站,https://baike.baidu.com/...aladdin)在中国,也有过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选边站”,砍掉“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学科、撤销机构、解散人员等的历史,人们记忆犹新,当属典型的例证。
现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本身是一种“政治任务”,也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但是,当一个学者进行哲学与科学的“研究”的时候,他必须尊重事实和规律。这就像法官断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中不能够掺和“政治站位”与“意识形态”;这与立法、司法、监法本身的政治目的和价值选择,不是一回事。我们在政治活动、社会治理当中,当然必须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但是在学术活动、探索未知当中,需要“谬误服从真理”的规则,不能够“举手表决,计算人数”、也不可以“下级服从上级”,等等。否则,大学教授、研究人员,擅长于“贴标签”就够了,还“坐十年冷板凳”干什么?
3. 如何肃清“斯大林哲学”的“流毒”?
“斯大林哲学”在中国至少流传了70多年。这里,举出近期两个斯大林哲学“流毒”非常之深的例子。
(1)在信息科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北京大学闫学杉教授,在出版《信息科学:概念、体系与展望》时,他在“前言”中“选边站”,正式明确地“表态”:“本书研究的是唯物主义信息科学。”“唯物主义信息科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因为“信息是物质的”。闫教授把“唯物主义信息科学”的对立面,说成是“唯信主义信息科学”,暗指其本质就是“唯心主义信息科学”,肯定属于被打倒之列。换言之,闫教授的意思是:他的信息科学是革命的、正确的,对立面的信息科学是反动的(或不革命的)、错误的。
(2)在信息哲学的研究领域,西安交通大学邬焜教授,在出版《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时,在第一章“时代、信息与哲学的变革”中说:“信息时代的信息也并不曾改变唯物主义的基本点:世界统一于物质。”“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第一个历史形式,而辩证唯物主义则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获得不同的具体规定性。”“现在国内哲学界…种种哲学新潮的涌现…呈现着的是一种全新变革哲学的趋势。”“而辩证唯物主义的信息哲学则可能成为这种全新综合哲学的一种具体形式。”
其实,闫教授和邬教授,他们连什么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能够干什么,一切的唯物主义都不能够干什么(有哪些像马克思所批评的局限性),都没有搞清楚。他们仅仅从自然科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常识”,去理解和使用“唯物主义”。
那么,什么是“唯物主义”,或者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唯物主义,就是在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中,主张“物质一元论”的“主义”。有一本哲学词典解释:唯物论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由物质组成的,物质的性质决定所有的其他东西,包括心的现象。”“所有形式的唯物论都拒斥抽象的存在而支持具体现实。唯物论一向是常识的同盟者并通常是决定论的。”笛卡尔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都没有了。”清华大学哲学家吴国盛教授说:“一切科学的对象都必须在时空中定位。不能够在时空中定位的,就不是个东西,研究它们的只能是‘伪科学’。”这样,“唯物主义”仅仅是支持“自然科学”的“主义”,它支持自然科学家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对象。这些对象都具有空间(长宽高、重量等)和时间特性,可以用肉眼和设备进行直接观察或者体验的,可以运用数量化、公式化的形式描述其运动轨迹。比如,无线电通信过程中导体内部的电流、电压、电阻之间的关系,以及电磁波传送的规律,等等。
“信息科学”,顾名思义,它是研究“信息”的科学。“信息”是什么?按照吴国盛教授的观点,信息肯定不是个“东西”;我们不妨称之为“东东”。因为,“智能手机”上的按钮一点,你的“东东”就传送到美国去了;这个东东肯定是不能“直接看见”、不能“直接感觉”的;它不能具有“体积”、“重量”、不能用时间(T)作为“参数”描述它的运动轨迹。这种在数字、字母、符号、表格、图形、照片、视频、音频之间来回转换的“抽象的东西”,还有敌军用密码编制的电文中的“信息”,用“物质的性质”怎么能够解释呢?而且生物基因信息和人类文化信息,与时俱增,是不守恒的。自然科学,不能够搞定这些“东东”;唯物主义是“哲学”,更加不能搞定它们。所以,闫学杉教授的“唯物主义信息科学”,等于说“哲学的科学”,比“辩证唯物主义”的术语还要荒唐,根本不可能产生、不可能存在!
邬焜教授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信息哲学”有可能经得起历史的“大浪淘沙”、继续存在吗?肯定不会。斯大林的哲学路线,连同他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一起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终结”了。作为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追随者,邬焜教授坚持斯大林哲学路线,继续在他的“博士点”、“硕士点”上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斯大林哲学的追随者。如果斯大林地下有知,他肯定是“乐坏了”。问题在于,我们亲爱的邬焜教授,把他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也给“害苦了”!
李宗荣在这里,还要进一步指出:在“斯大林哲学”的“流毒”之后,闫学杉教授、邬焜教授的理论,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它们自己的新“流毒”:比如,华中科技大学语言学教授张XX,按照“信息论”,“信息学”思考,都失败了;华中科技大学法学教授李X,按照所谓“信息哲学”的思路走,也是无功而返。限于篇幅,这里不说远了。
回到本文的主题,具体地说,如何能够肃清斯大林哲学(教科书哲学)在中国哲学界与科学界的“流毒”呢?
围绕哲学教科书的“教学”主题,我们可以将全部的人员一分为二:“无关人员”(即完全没有接触过教科书哲学的)和“有关人员”(即与教科书哲学有关系的)。我们这里不讨论无关人员。对于有关人员,我们又一分为二:“过去有关”(即过去学过教科书哲学,但是现在不是从事其教与学的)和“现在有关”(即现在正在从事教科书哲学的教学活动的)。我们将现在有关的人员再“一分为二”:哲学教科书教学中的“教授”和教学中的“学生”。
这样,我们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针对三种人员,讨论如何肃清斯大林哲学的流毒:(1)教科书哲学教学中的“教授”;(2)教科书哲学教学中的“学生”;(3)学习过教科书哲学,但是现在没有从事相关教学活动的全部其他人员。
首先,“教科书哲学”的教授们,他们需要认清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斯大林哲学在苏联,早就不存在了。在“马工程”教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名单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斯大林了。一些博导、硕导、学士导师,继续追随“斯大林哲学”,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前途了。邬焜教授的“辩证唯物主义信息哲学”,研究了三四十年,这一下子“改口”,该怎么说呢?如何向已经毕业的和在读的同学们做出他的学术交代呢?真是需要积极的心态和超常的智慧。“斯大林哲学”也可以不讲了,因为什么原因由教授自己说。通常,教授有权自己选定课程教材,设计教学内容,达到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目的”。依据马克思关于“新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他自己的“文本”,讲授“马克思哲学”,对于原有教材进行修订,或者新编《马克思哲学》教材,显然属于教学管理部门的肯定和鼓励的范围。
其次,“教科书哲学”的学生们,这些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应当像康德所说的那样,积极主动地自己把自己当“目的”,而不是“工具”。需要替自己的将来想一想,继续追随斯大林哲学的结局将会是如何?他们自己以后的学术发展方向、业务领域中的晋升等等,应当由他们自己设计和实践。所以,学生们也可以向课程教授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就算教授听不进去,学生们也可以自己自学,选读马克思哲学的相关文本,教授是无权干涉的。
第三,学习过教科书哲学,但是现在没有从事相关教学活动的全部其他人员。这些在“教科书哲学”的训练之下走过来的“过来人”,他们虽然没有继续围绕哲学教科书而工作,但是他们受到了教科书的“熏陶”,至今记忆犹新,他们都有必要在头脑里划清自己与斯大林哲学的界限,用马克思本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观察自己的生活、学习与工作。这种挑战本身也是一种机遇,让我们有机会经过一场“信息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洗礼”。特别是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同志,时间多多,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我们顺其自然,乐在其中,何其妙哉!
参考文献
[1]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2] 艾思奇.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3] 邬焜. 信息哲学:概念、体系、方法.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4] 闫学杉. 信息科学:概念,体系与展望.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
[5] 李宗荣. 理论信息学概论.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6] 田爱景. 论信息社会特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医学信息,199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