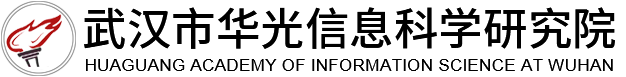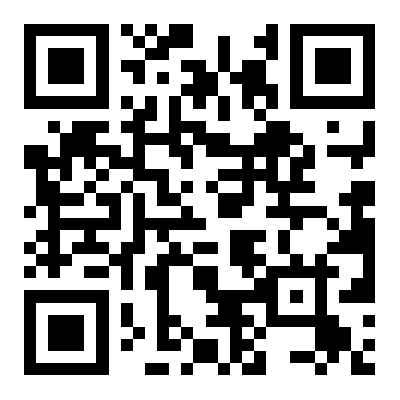本院成果展示
李凌斌,李宗荣:破解“心身关系”的二元论哲学与科学的途径
破解“心身关系”的二元论哲学与科学的途径
李凌斌1,李宗荣1,2
1 武汉市华光信息科学研究院
2 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摘 要:我们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宗教、哲学与科学,都在研究自然界、社会与人类思维,仅仅使用的方法不同,因而各自的结论相去甚远。宗教的方法是猜想、信仰。哲学的方法是逻辑和语言分析。科学的方法是实验和验证。信仰是人类的精神动力、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哲学中也有猜想,其预设前提就是一种信仰。科学当中,也讲语言的逻辑,但是更要求实证。这样,在“心身关系”问题上,可以开展各类宗教、哲学与科学的讨论。本文的讨论不涉及宗教,仅仅从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的视角展开。
在逻辑上,笛卡尔区分“可思之物”与“延展之物”,是完全必要的;它们有各自独立的“因果链条”,的确属实。但是,认定它们两者绝对地相互独立,是错误的。我们运用“理论信息学”的“物质-非物质”二重性的理论,承认“心灵”与“神经”两者逻辑独立,实际依存,问题就解决了。在科学的意义上破解心身关系,需要在神经科学和信息科学的领域同时工作,找出各自的“因果链条”,并且说明两者之间的具体联系。由于人脑研究者不能像电脑设计师那样,将神经系统拆开来分析,然后组装,我们预计,真正解开心身关系中的“硬件”谜团,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关键字: 心身关系,柏拉图,笛卡尔,物质-非物质二元论,信息哲学
 第一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简介
李凌斌,男,1973年1月生,中国汉族。现任美国阿米福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阿米福集团投资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院学士:湖北工业大学硕士:加拿大 O’Sullivan 学院互联网编程。曾在加拿大运营零售及餐饮企业,后来从事北美房地产与商业管理,具备实战管理能力与国际视野。兼任中国武汉市华光信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发表《从人类智能、机器智能,到万物智能、万物互联》、《关于李宗荣诉金新政案的“证据”分析》等论文。
一、引 言
1.给创新者以一个包容的学术氛围,防范“先知悲剧”
我们主张,为了推进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的发展和完善,应当给创新者以一个包容、宽松的学术氛围,防范“先知悲剧”带来的不幸。因为,彻底颠覆传统、实现从无到有的创造,即完成“从0到1的跨越”,它越是伟大,可能除了它的成就之外,其中观念与理论的缺点和短板可能越多。
柏拉图的晚年就曾经怀疑自己创立的理念论,这成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推倒理念论的原动力之一:连你自己都没有“底气”了,可见理念论靠不住。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首次提出,能量只能取基本单位的整数倍,即量子化的概念。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着的物质和能量都是“连续”的,相信“自然界无跳跃”。所以,量子概念理所当然地遭到许多物理学家的反对。这时,普朗克自己也动摇了,他后悔当初的大胆,甚至放弃了量子论;他继续用能量的连续变化来解释辐射的问题。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世时发表的文章,都是与语言学主流思想一致的,而他自己在课堂上的讲述,却是“离经叛道”的,但他从来没有发表,也没有准备发表。在他过世之后,他的几位学生整理听课笔记和索绪尔的若干手稿,发表了他的语言学著作。但是学术界起初不愿意相信这本书;经过几十年的专家考证后,证明那的确是索绪尔本人的思想,而且是合理的,然后才被广泛接受。
我们认为,在原则上,柏拉图与笛卡尔提出的心身关系的理论是合理的。它们之所以遭到质疑和排斥,原因很多,其主要因素是:未能恰当地解释“心灵”的本质,它如何与“身体”相处,以及如何相互作用。
2.二元论基础上的信息哲学破解“心身关系”
笛卡尔定义了两个“实体”或者“实在”,是正确的。认为心灵是“可思之物”,没有延展,身体是延展之物,不能思维。从本质和功能上说,他是正确的。计算机硬件有延展,它本身不能思维;能够思维的是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各类应用软件。但是,笛卡尔定义“实体”是“一个除了自身存在之外什么也不需要的存在之物”,他有合适的理由,也有缺点。如果坚称两个“实体”绝对独立、互不需要,造成解释心身关系的麻烦,导致笛卡尔的“松果腺”,成为质疑者的“口实”。
我们认为,笛卡尔定义,在“延展之物”与“可思之物”各自的逻辑链条分离而且封闭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两者各自内部的运行的确不需要对方的介入。但是,在“延展之物”与“可思之物”两者的关系上,该定义是错的;因为,可思之物需要物质“载体”,延展之物需要在“思维”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换言之,任何信息系统都需要“物质”作为“载体”,还需要“物质能”作为“载能”。“可思之物”以“神经系统”为“载体”,以大脑的“生物能”为“载能”。于是,“心”和“身”,在心灵和神经的“关系”上,像一枚“硬币”那样,“一体两面”;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不同的侧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换言之,心和身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这样一来,关于心身问题讨论的各种“主义”,几乎都有各自的合理性。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寻找解决心身问题的一般途径”。
“理论信息学”认为,宇宙万物都具有“物质-信息二重性”,其存在的方式和状态,运行的动力和机理,都是“二重性”的。物质的原则和信息的原则,物质的因果链条和信息的因果链条,各自封闭;两者并行不悖。机械、电子、生物、人脑,如维纳控制论所说,工作的原理都是一样的。这样,我们的“身体”,既可以由“心灵”指挥,同时又受生物、化学和物理学的“能量”所推动。因为心灵的载体是神经系统,信息的“力”与物质的“力”在逻辑上一分为二,在物理上合二为一。于是,根本没有必要像笛卡尔那样,设置一个“松果腺”来存放两类不同的“实体”;否则,人家要进一步地追问:在松果腺内部,两者如何相处、如何作用呢?
3.关于心身关系的四个实际案例
本文列举下面四个心身关系的实际案例,用来作为分析和解释心身关系的基础。
(1)幼儿用“手指头”计数并运算“2+3=5”。他左手伸出2个指头,右手伸出3个指头,然后合在一起,点数,得到结果,指头显示5。
(2)用珠算计算“7+8=15”。在算盘左边拨算珠“7”,在右边拨算珠“8”,然后在“7”上“加8”,口诀“8去2进1”,于是得到结果,算珠显示“15”。
(3)运用计算机求解一元二次方程“x2-4x+4=0”的根。根据求根公式x= [-b±√(b^2-4ac)]/2a,(a=1,b=-4,c=4),编制计算机程序,得到结果x=2。验算:22-4×2+4=0。然后,打印:问题,程序,结果,验算。
(4)考生填报高考升学的志愿。他的分数可以上任何一所国内的大学;他憧憬空天事业,喜欢自动化;于是决定:填报第一志愿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专业。
无论是个人思维,还是人-机联合,都由系统的“硬件”(延展之物)与“软件”(可思之物)相互分工,完美配合。“信息”,以个人的肢体、神经,计算机的硬件设备的物质为“载体”;“智能”以人类肌肉的、神经的、计算机的能量为“载能”,实现信息处理的“IPO”(Input-Process-Output)过程。
4.信息科学如何破解心身问题
我们认为,如果说“哲学无定论”,那么科学是有“定论”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物理学”说,两斤重的铁球从高处落地,比一斤中的铁球快一倍。但是,在“科学物理学”的“斜塔实验”中,大小铁球同时落地。在一个真空管里,人们看到“鸡毛”和“铁球”同时下落。问题的关键是,科学要求符合客观实际,理论自恰,而且实用。李宗荣说,信息科学≠信息哲学;上述信息哲学对于“心身问题”的解释,不是信息科学的解释。
与“信息哲学”相比,如果我们从“信息科学”的视角讨论“心身关系”,那么问题要复杂得很多。因为,作为“科学”的讨论,不能仅仅是语言的形式分析和逻辑的推理论证,我们必须设计、解剖具体的心和身的“IPO”过程,用实验验证关于“心身关系”的主张。比如,在上述“手指计算”、“算盘计算”、“电脑计算”和“头脑计算”中,“数据”的存储肯定有确切的物理位置,与指头和算珠不同,要说出是哪几条神经存储“7”,“8”和结果“15”。考生的“大学之梦”、“知识存储”、“分析判断”,都在哪些神经元发生?
李宗荣在早期的程序设计中,由于在存放系统软件之后,当时整个计算机“内存”可用空间是有限的,需要仔细分配。比如,数据地址(初始数据,中间数据,结果数据),程序地址,以及内存可用空间的占用、覆盖等等;这,相当于直接在计算机的“神经”的级别上工作。由于计算机硬件工程师,对整个硬件系统一清二楚,当然可以告诉软件工程师,他们可以使用的存储器的地址范围。但是,我们的脑科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计算机硬件工程师这样的水准?
显然,只有脑科学与神经科学的专家,才可能知道“7”、“8”和“15”在人脑神经系统中的具体位置。但是,从目前的神经认知科学的发展状态看,连人们的“意识”发生在大脑的“前部”,还是“后部”,都可能没有搞明白,要落实到某几根神经的位置,恐怕要到猴年马月。而且,鉴于科学研究的伦理学限制,人类不能把神经系统像计算机零件一样,拆开重装。神经科学家也不能拿小白鼠和兔子作为“替代物”,因为人脑与动物脑区别太大,而且人脑的语言文字处理系统,动物们根本没有。所以,指望脑科学与神经科学完全搞个明白,恐怕近几代人都难得有机会看到。
5.参考文献
[1] (德)马丁·摩根史特恩,罗伯特·齐默尔.哲学史思路----穿越两千年的欧洲思想史.唐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李宗荣.理论信息学概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