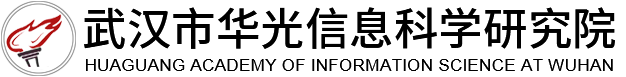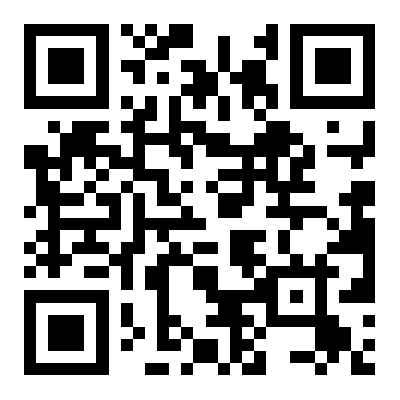网站首页 >> 2025 SIS 展示 >> 张雁冰:信息科学的哲学审视:基于本体论与
2025 SIS 展示
张雁冰:信息科学的哲学审视:基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发展综述
信息科学的哲学审视:基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发展综述
张雁冰1,2
1.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2. 武汉市华光信息科学研究院
摘 要:信息科学作为跨学科的“元科学”,在社会与技术领域影响深远,但其哲学基础仍显薄弱。本文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两条主线梳理信息科学的发展,揭示其从客观主义到建构主义、从还原论到整体论的演化逻辑。批判性分析表明,当前存在三大问题:数据、信息与知识概念混乱;算法中心化削弱主体性;效率与预测逻辑下,公平、隐私与福祉等价值缺失。针对这些不足,本文提出四个未来方向:发展分层本体论以澄清数据—信息—知识关系;构建 “人–机–环境”协同认识论以增强认知与可解释性;推进价值敏感设计以嵌入伦理与社会责任;探索信息与现实的形而上学联系。本文呼吁跨学科合作,推动信息科学实现技术与价值的统一。
关键词: 信息科学,本体论,认识论,建构主义,价值敏感设计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张雁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工智能博士研究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嵌入式硕士)、西南交通大学(工管学士),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兼修管理心理学。曾任阿里巴巴数据科学家/大数据高级专家、文化科技集团CEO,主导新零售、数据中台与数据安全等标杆项目。研究聚焦持续学习与记忆、NLP与多模态视觉、LLM应用。技术方面精通PyTorch、 MLFlow 、BERT/GPT/Swin-Transformer及Hive/Flink/Neo4j,具备Java/Python全栈与亿级数据架构能力,获多项AI专利。管理方面具10+年团队与战略经验,贯通技术—产品—市场—融资链条,擅长将前沿算法产业化落地。
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
在数字化与智能化驱动下,信息科学已成为跨学科的”元科学”,既支撑工程与自然科学,也深刻影响社会与人文学科;信息作为数据、意义与价值的载体,正塑造知识生产与社会组织的方式[1]。与此同时,”效率—预测—可控性”的技术叙事在实践中占据主导[26],使关于”信息是什么””如何被认识与使用”的哲学问题长期被边缘化[6, 14],并由此引出一系列现实挑战,如算法偏见、信息茧房与隐私风险等[29, 30, 34]。为回应上述张力,本文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两条主线展开:其一,梳理信息概念从”客观量”到”概念表征”再到”情境生成”的历史转向,明确数据—信息—知识的区分与联系[7, 31, 32];其二,审视从”反映—表征”[37]到”建构—具身”[8]的认识论演变,强调主体、情境与实践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10, 35]。本文据此指出:要走出工具理性主导的局限,信息科学需在理论与应用层面同时转向——在基础层面澄清概念与范畴[5],在方法层面引入面向”人—机—环境”的协同与可解释性框架[12],在价值层面将公平、隐私、问责与福祉内生化于系统设计与治理[15, 16]。
1.2 研究问题
RQ1(本体论):信息”是什么”?经典信息论将其界定为消除不确定性的量[32],刻意排除语义/语用[2];知识工程把信息落实为显式概念与形式化本体[28];当代强调主体—情境—实践
中的意义生成[13, 36]。本文比较三种立场,澄清数据—信息—知识的范畴边界与生成机制[4, 9],避免概念混用与层级错置[10, 16, 19, 20]。
RQ2(认识论):人/机如何”知道并使用”信息?从”反映—表征”的被动接收,转向”建构—具身”的主动生成;同时审视推荐与预测系统在塑造注意、偏好与选择中的作用及其对主体性的影响[3],以及监视资本主义机制下的主体性削弱[10, 35, 40]。
RQ3(范式与实践):不同哲学立场如何塑造研究与应用?工具理性偏向效率与预测,价值理性强调公平、隐私、问责与可解释性[18, 27]。本文据此提出面向”人—机—环境”的协同框架与价值敏感设计路径[17],主张在模型、数据与交互全流程内生化约束与解释[15, 24, 29]。
1.3 研究意义与贡献
理论意义:梳理信息的多维属性,比较客观论—概念论—建构论的差异,提出数据—信息
—知识的可操作区分与动态生成视角[7, 16, 31]。 综述意义:以”三阶段”框架[23]整合经典信息论、知识工程与情境/具身转向,揭示从”量化传输”[38]到”符号表征”再到”情境建构”的范式演进[19, 32]
1.4 论文结构
第2节:理论框架(本体/认识论与范式互动);第3节:发展阶段综述(经典信息论—知识工程—情境化);第4节:批判性反思(概念、主体、价值、跨学科);第5节:未来方向(分层本体、人—机—环境、VSD、形上探讨);第6节:结论与启示。
2 理论框架:信息科学的哲学基础
信息科学的哲学基础主要体现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双重维度[21]。
2.1 本体论视角:从客观主义到概念主义再到建构主义
信息科学的本体论经历”客观论→概念论→建构论”的历史转向,深刻塑造了学科的基础与
范式[52]。
2.1.1 客观论(Objectivism)
早期将信息视为客观、可量化之物:香农把信息界定为”消除不确定性的量”,有意剥离语义/语用,使之成为可度量、可传输的客观量[32];维纳进一步强调”信息既非物质亦非能量”,确立其独立研究地位,体现还原与量化取向[38]。这一观点与中国学者对信息本质的讨论形成呼应[53, 54]。
2.1.2 概念论(Conceptualism)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知识工程与 AI 发展,”本体论”被操作化为领域概念模型;信息被理解为结构化符号/概念网络,支撑知识图谱、语义网与专家系统等实践[45]。其核心假设是世界可由逻辑符号精确表征,人机认知依赖一致的概念化与形式化[19, 20]。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体现了信息科学的系统性特征[42, 43]。
2.1.3 建构论(Constructivism)
进入 21 世纪,认知科学与情境取向影响加深:信息被视为主体—情境—实践互动中”被建构的意义”,而非先在实体;Dervin 的”意义建构”强调面向问题的情境生成,Floridi 的”信息实在论”则赋予信息理解现实的基础地位[10, 16]。由此,本体论脉络由”量化/静态”走向”生成/整体”,完成从客观量到符号结构再到语境生成的转变[44, 46]。
2.2 认识论视角:从反映论到表征论再到建构论
认识论聚焦”人类与机器如何认识并运用信息”。随学科演进,其立场由反映论转向表征论,再到强调主体与情境的建构论,对应了从”镜像映射”到”符号操作”,再到”情境生成”的连续转型[51]。
2.2.1 反映论(Reflectionism)
以通信模型为代表:知识被理解为从信源到信宿的准确传送,主体多处于被动接收位置;该立场与逻辑实证主义及控制论并行,强调可验证性与准确性,但忽视信息在语义与使用情境中的复杂性[32, 37]。这种观点在东方学术传统中也有相应的讨论[47]。
2.2.2 表征论(Representationalism)
20 世纪 80 年代起,知识工程与 AI 推动”符号—逻辑”取向:信息被界定为以形式语言编码的知识体系,”本体论即显式概念化规范”的主张将认识过程转化为在规则之上的抽象与操作;信息系统被视为人机共享的符号处理平台,依赖一致的概念化与形式化。然而,该取向过度静态,难以处理语境依赖与动态更新[19, 20, 28]。
2.2.3 建构论(Constructivism)
进入 21 世纪,认识论转向主体—情境—实践的生成过程:信息被视为为行动而建构的意义,而非被动反映或静态表征;”意义建构方法论”凸显用户在具体问题情境中的主动生成;具身/在世视角强调感知—行动—环境的循环互动;信息认知被理解为动态、交互、生成的过程,为人机关系、可解释性与情境交互提供哲学支撑[10, 16, 35, 36]。这一转向体现了信息认识论的深层变革[48, 50]。
2.3 哲学与科学的互动:范式演进与信息的多维性
信息科学并非仅是技术与应用的集合,而是哲学与科学双向塑形的产物:哲学思潮为理论框架提供前提,方法与技术的迁移反过来推进范式更新。借助 Kuhn 的“科学革命”视角,可将学科发展理解为经历范式形成—危机—转换的循环;而“信息”的多维属性正是推动转换的重要动力[23]。
2.3.1 范式演化与哲学支撑
学科史可概括为三次连续转向:从香农信息论主导的“量化传输范式”,到知识工程巩固的“符号表征范式”,再至认知科学与信息哲学引导的“情境建构范式”。相应地,早期由实证主义与反映论支撑,中期由逻辑实证与符号主义加强,近阶段则由建构主义与情境/具身认知奠基的人本与价值导向进一步强化[10, 16, 19, 20, 32, 36]。
2.3.2 信息概念的多维性
“信息”具备互补而张力并存的维度:物理维度将其刻画为熵/不确定性之量[32];符号维度把它实现为可操作的知识表征[19, 20];认知维度视其为主体进行意义建构的资源[10, 13];社会维度将其置于权力、正义与伦理的结构中[6, 15]。因此,厘清范式更替背后的哲学动力并系统整合上述多维概念,是后续研究的理论前提与方法起点。
3 信息科学的发展阶段: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双线索综述
本章以本体论与认识论为双主线,系统梳理信息科学的阶段性演进。学科的发展并非线性技术累积,而是哲学立场与科学实践相互塑形的过程。我们聚焦三个关键时期:经典信息论、知识工程与系统时期、认知与情境化时期,以揭示从“客观量化—符号表征—情境建构”的连续转型[23]。
3.1 经典信息论时期(1940s–1970s)——客观本体与传输认识论
20 世纪中叶,在通信工程与控制论的推动下,信息科学进入奠基阶段。其核心在于将信息视作客观、可量化的实体,为工程与自然科学的深度耦合提供了统一度量与理论工具[32,38]。本体论层面:香农提出信息熵,以概率形式刻画“消除不确定性”的量,刻意剥离语义与语用,使信息成为独立于主体的可测属性[32];维纳进一步强调“信息既非物质亦非能量”,将其确立为独立研究对象,体现还原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取向[38]。
认识论层面:香农—韦弗模型将信息处理抽象为“编码—传输—解码”的数学过程,强调在噪声最小化下的准确传递与效率最优,主体被置于被动接收位置,意义与价值被有意排除在模型之外[37]。
局限性:将信息约化为熵的统计模型难以区分“有意义的信息”与“无意义的噪声”,难以处理意义与情境[2];同时忽视社会与价值维度,为后续“意义/价值”反思埋下张力[7]。
3.2 知识工程与系统时期(1980s–2000s 初)——概念本体与表征认识论
20 世纪 80 年代起,信息科学出现明显的“知识转向”。研究焦点由通信与信号处理扩展至
知识工程与语义建模:信息不再仅是可量化对象,而被提升为结构化表征。
本体论层面:出现“概念本体”的操作化理解。Gruber 将本体论界定为“显式的概念化规范”,以逻辑语言刻画领域知识,支撑跨系统共享与复用[19];Guarino 推f进形式本体的理论化,强调概念层级的清晰与一致[20]。此时的信息被理解为符号化、逻辑化、可操作的结构系统,其基础延续理性主义与逻辑实证传统。
认识论层面: 研究重心转向“表征— 推理” 模型: 知识经由符号系统表征, 并在知识库上实施基于规则或图式的推理。典型如医学专家系统 MYCIN,以知识表示与推理机制支撑领域决策[33]。这一思路在语义网与早期知识图谱中进一步发展,信息系统被理解为人机共享的符号操作平台,知识逐渐被物化为可操控的“资产”。
局限性:其一,静态表征与严格形式化难以应对知识的动态性与模糊性,在开放环境中易显僵化与脆弱[5,28];其二,表征与推理的割裂,使系统在处理情境依赖与跨域知识时力有未逮,这为后续建构主义与情境认知取向的兴起奠定背景[6]。
3.3 认知与情境化时期(2000s–至今)——建构本体与建构认识论
进入 21 世纪,信息科学在认知科学、现象学与情境取向影响下迎来又一次转折:信息被重
新界定为主体与情境互动中生成的结果,而非先在的客观量或固定符号体系。
本体论层面:信息呈现明显的主体/情境依赖性,其意义在认知者与环境的动态交互中逐步建构,强调生成性(becoming)与关系性(relationality)[13]。Floridi 的“信息实在论”主张信息既是知识建构资源,也是理解现实的基本形态,为该时期的本体论探索提供哲学支撑[7,16]。认识论层面:研究转向具身化与建构化模型。Dervin 的“意义建构方法论”强调个体在具体问题情境中的主动生成[10];具身认知进一步提出“在世”/embodiment 的循环结构,认为认知是感知—行动—环境的交互过程[35,36]。信息系统由“传输/表征装置”转而被理解为认知环境的一部分,其设计目标从单纯追求效率与准确,拓展为支持意义建构、交互实践与可解释性[12, 24]。
开放问题:一方面,“建构性信息”的哲学阐释与数据—算法的工程依赖之间存在错位[5];另一方面,伦理、隐私与公平等价值尚未充分嵌入技术实践,需要以价值敏感设计与信息伦理为抓手,缩小“哲学理想—工程现实”的差距[15,27]。
4 批判性反思
信息科学一方面推动技术与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哲学根基与实践应用的多重缺陷。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理性与跨学科四个维度加以反思, 旨在为后续的理论重构与制度化实践提供支点。
4.1 本体论的混乱与缺陷:数据—信息—知识边界失范
信息科学在本体层面长期存在数据/信息/知识(DIK)概念的重叠与混用,既削弱理论一致性,也影响工程可操作性。Ackoff 的层级模型[1]与 Davenport&Prusak 的经验—判断取向为三者区分提供了启发,但在实践中“大数据”语境常将数据与信息互换使用,模糊层级与语境条件[4,31]。学科间的语义漂移亦加剧分歧:通信工程将信息等同为熵的度量,刻意排除了语义与语用[32];而管理与社会科学多将信息视为知识生产的前阶段与输入要素[4]。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知识工程中信息被过度简化为可操作的符号结构,忽视其语境依赖与价值承载[5,7]。要缓解上述张力,亟需在多维一致性的原则下,给出可检验的层级划分与跨域对齐标准。
4.2 认识论的人本缺失:算法中心化与主体性削弱
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推动的“相关性优先”范式,强化了以预测与自动化为中心的认识模式,使主体被还原为可计算的行为模式,意义建构与价值判断被边缘化[26]。在“监视资本主义”机制下,平台通过持续收集与建模将注意与选择前置化、可预测化,从而压缩个体的自主性与反思空间[40];推荐系统的个性化筛选进一步制造“过滤气泡”,削弱跨观点的信息接触[30]。结果是,“预测即认知”的狭隘立场扩张为事实上的治理逻辑,主体在信息世界中的解释权与能动性被动萎缩[15,29]。因此,有必要以人本—协同认识论矫正算法中心化,重申主体在意义生成、情境判断与责任承担中的地位[10,35]。
4.3 价值理性的忽视:效率/预测优先下的公平、隐私与福祉缺位
以效率与预测为核心的技术理性提升了系统性能,却系统性地压低了公平、隐私、问责、福祉等价值维度的优先级。机器学习在教育、就业与司法等高影响场域的部署显示:若缺乏制度化的价值约束,模型性能指标可能与结构性不平等共存甚至相互强化[29]。隐私方面,数据采集与追踪的常态化重塑了个人—机构的权力结构,风险并非仅是泄露,而在于长期、不可见的画像与操控[15, 34]。福祉层面,基于预测—控制的设计逻辑往往忽略人的整体发展与能动性[40]。对此,信息伦理与价值敏感设计(VSD)主张将公平、透明、问责与福祉内生化到数据、模型与交互全流程之中,形成可审计、可追责的技术—制度组合[15,27]。
4.4 跨学科张力:与认知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的脱节
信息科学的跨学科属性在专业化进程中转化为新的张力: 其一, 与认知科学的分歧在于 “计算—表征”框架难以吸纳具身与情境转向的洞见,导致对主体性与体验维度解释不足[35, 36];其二,与社会科学的割裂使信息系统难以有效回应权力、阶层与文化差异,进而在茧房、鸿沟与偏见等议题上缺乏可操作的干预框架[4,7];其三,与哲学的互动不足使“信息是什么/如何被认识”的根本问题长期悬置,削弱了学科统一性与自反能力[5,15]。面向未来,需要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域协作:以具身—在世的认知框架联通人机交互与可解释性研究,以社会—制度视角嵌入治理与审计,以信息哲学提供本体—认识的一致化基底[13,15]。
5 未来发展方向
在回顾信息科学的哲学基础与阶段性轨迹后,未来的发展需在本体—认识—价值三层同步
深化与重构,使学科在复杂社会与智能环境中兼具理论前瞻性与实践指导力。
5.1 分层本体论:以动态生成视角重构 DIK 关系
DIKW 框架提示数据—信息—知识的层级性,但其线性与静态假设难以刻画情境与实践[Rowley2007,
Bawden2012]。未来可将数据视为潜在载体,信息视为在语境中被解释与加工的中介,知识视
为经由经验与判断生成的高层结构,并以跨域约束与可检验划分消解混用与割裂[5, 7]。该动态
—分层本体论为模型、数据与应用提供统一语义地基。
5.2 人—机—环境协同认识论:从交互走向融合
传统 HCI 的工具—界面范式已难适配智能环境。应以人—机—环境协同认识论重构研究:承认行动嵌入情境、策略即时生成[35],以认知增强为目标设计human-in-the-loop流程,并将可解释性与信任校准内生化到任务与界面之中[12, 24]。由“传输/表征装置”转向“认知生态一部分”,将提升系统的鲁棒性与可用性[13]。
5.3 价值敏感设计(VSD):把公平、隐私与问责嵌入全流程
性能至上的技术理性易压低公平、隐私、问责、福祉的优先级[15, 29]。VSD 主张在需求
—数据—训练—部署—审计的全生命周期显式编码价值约束,形成可审计与可追责的制度—技术组合[27]。在推荐与预测系统中,需以可解释性与透明支持利益相关者监督,平衡效率与正义[12,24]。
5.4 信息与现实的形上学:信息计算论与万物计算论的对话
信息科学可进一步探索信息—现实的形上学接口:信息计算论将宇宙刻画为持续的信息—计算过程,强调结构—演化的一体性;万物计算论主张自然界可被视为普适计算系统[11,39]。尽管存在争议,这些取向拓展了信息科学的理论边界,并为与物理学与计算哲学的对话提供桥梁[16]。
小结 未来突破将围绕:动态分层本体、协同认识论、VSD 治理与信息—现实形上学展开。它们共同回应概念混乱、主体性削弱与价值缺位等难题,为信息科学在技术—社会双重挑战中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6 结 论
信息科学作为跨学科的“元科学”,其历史是哲学基础—科学实践互动演化的进程:理论反思与工程应用相互牵引,同时也出现错位与滞后。本文从演化逻辑、实践困境、价值转向与跨学科协作四方面加以总结与指向[4,31]。
6.1 从客观主义到建构主义:由还原论走向整体论
学科演进可概括为“客观量化→符号表征→情境建构”的连续转型:香农以不确定性减少奠定客观量化与实证基调[32];知识工程通过形式本体与符号系统推动逻辑化建模[19,20];当代转向主体—情境的意义生成与信息实在论,强调生成性与关系性[10,16]。由此,本体/认识框架由还原—静态过渡到整体—生成。
6.2 哲学基础滞后与实践困境
技术跃迁伴随哲学滞后,带来偏见、茧房、隐私侵蚀等系统性风险:性能—效率导向使算法歧视与结构性不平等被放大[29];个性化筛选造成“过滤气泡”,削弱多元接触[30];数据画像与追踪重塑权力结构,隐私风险呈制度化[34]。缺乏统一本体与多维认识支撑,学科过度依赖预测逻辑,忽略公平、透明与责任[15, 40]。
6.3 从“是什么”到“应该是什么”:价值转向
未来突破应由“信息是什么”扩展为“信息应该是什么”。信息伦理强调将尊严、隐私、公平、福祉嵌入系统目标与机制之中,形成可审计与可追责的规范[15,27]。相应地,研究范式需由工具理性转为兼容价值理性的综合框架,平衡效率、可解释性与社会可接受性[12,24]。
6.4 迈向跨学科合作
“信息”的多维性决定了跨域整合的必要:任何单一学科难以独立解决本体、认识与治理的联动难题[7]. 面向未来,应以问题为导向构建信息科学、认知科学、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协作共同体:以具身/情境认知联通人机与可解释性[13, 35],以治理与审计机制嵌入社会—制度层面[15],以信息哲学提供一致化的本体—认识基底[16]。如此方能实现整体化、价值敏感、可持续的信息科学。
参考文献
[1] Russell L. Ackoff. “From data to wisdom”. In: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16 (1989), pp. 3–9.
[2] Yehoshua Bar-Hillel and Rudolf Carnap. “Semantic information”. In: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4.14 (1953), pp. 147–157.
[3] Solon Barocas and Andrew D. Selbst. “Big Data’s Disparate Impact”. I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04.3 (2016), pp. 671– 732.
[4] David Bawden and Lyn Robinson.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cience.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2012.
[5] Mark Burgin. Theory of Information: Fundamentality, Diversity and Unifica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0.
[6] Rafael Capurro.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In: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7.2 (2009), pp. 125–141.
[7] Rafael Capurro and Birger Hjørland.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In: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3).
[8] Andy Clark. Being There: Putting Brain, Body, and World Together Aga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9] Thomas H. Davenport and Laurence Prusak. Working Knowledge: How Organizations Manage What They Know.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8.
[10] Brenda Dervin. “Sense-ma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 overview of user interests in knowledge seeking and use”. In: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2 (1998), pp. 36–46.
[11] Gordana Dodig-Crnkovic. “Info-computationalism and morphological computing of informational structures”. In: In- formation 3.2 (2012), pp. 204–218.
[12] Finale Doshi-Velez and Been Kim. “Towards a rigorous science of interpretable machine learning”. In: arXiv preprint arXiv:1702.08608. 2017.
[13] Paul Dourish. Where the Action Is: The Foundations of Embodied Inter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14] Luciano Floridi. “Open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In: Metaphilosophy 35.4 (2004), pp. 554–582.
[15] Luciano Floridi. The Ethics of In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 Luciano Floridi.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7] Batya Friedman, Peter H. Kahn Jr., and Alan Borning. “Value Sensitive Design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n: The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thics. Wiley, 2008.
[18] Batya Friedman, Peter H. Kahn Jr, and Alan Borning. “Value sensitive design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6 (2006), pp. 348–372.
[19] Thomas R. Gruber. “A translation approach to portable ontology specifications”.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 Vol. 5. 2. Elsevier, 1993, pp. 199–220.
[20] Nicola Guarino. “Formal ontolog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n: Proceedings of FOIS’98. IOS Press, 1998, pp. 3–15.
[21] Wolfgang Hofkirchner. Emergent Information: A 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Framework. World Scientific, 2013.
[22] Wolfgang Hofkirchner. Emergent information: A 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framework. Vol. 3. World Scientific, 2012.
[23]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4] Zachary C. Lipton. “The Mythos of Model Interpretability”. In: arXiv (2016). arXiv: 1606.03490 [cs.LG].
[25] Fritz Machlup. “Semantic quirks in studies of information”.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s. Ed. by Fritz Machlup and Una Mansfield. New York: Wiley, 1983, pp. 641–671.
[26] Viktor Mayer-Scho¨nberger and Kenneth Cukier.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Boston: Eamon Dola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27] Brent D. Mittelstadt et al. “The ethics of algorithms: Mapping the debate”. In: Big Data & Society 3.2 (2016), pp. 1–21.
[28] Allen Newell. “The knowledge level”.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8.1 (1982), pp. 87–127.
[29] Cathy O’Neil.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16.
[30] Eli Pariser.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31] Jennifer Rowley. “The wisdom hierarch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IKW hierarchy”. I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33.2 (2007), pp. 163–180.
[32] Claude 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3 (1948), pp. 379–423.
[33] Edward H. Shortliffe. Computer-Based Medical Consultations: MYCIN. New York: Elsevier, 1976.
[34] Daniel J. Solove. Understanding Priv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5] Lucy A. Suchman. Plans and Situated Actions: The Problem of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6] Francisco J. Varela, Evan Thompson, and Eleanor Rosch.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 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37] Warren Weaver.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9.
[38] 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MIT press, 2019.
[39] Stephen Wolfram. A New Kind of Science. Champaign, IL: Wolfram Media, 2002.
[40] 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9.
[41] 姜璐 and 李宗荣. “信息能:信息世界运动变化的真正动力——兼评《物信论——多层次物质信息系统及其哲学
探索》”. In: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1.1 (2007), p. 5.
[42] 李宗荣. “理论信息学:概念,原理与方法(I/VI)”. In: 医学信息 017.012 (2004), pp. 773–785.
[43] 李宗荣. “理论信息学:概念,原理与方法(II/VI)”. In: 医学信息 018.001 (2005), pp. 1–10.
[44] 李宗荣. “理论信息学:概念,原理与方法(III/VI)”. In: 医学信息 018.002 (2005), pp. 73–81.
[45] 李宗荣. “理论信息学:概念、原理与方法”. PhD thesis.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46] 李宗荣. “理论信息学:概念、原理与方法(IV/VI)”. In: 医学信息 (2005).
[47] 李宗荣. “论信息科学的世界观(I/V)”. In: 医学信息 21.8 (2008), p. 11.
[48] 李宗荣 and 田爱景. “从”我思故我在”到”社会思故社会在”——兼谈社会认识论与社会信息科学的逻辑出发点”. In: 医学信息 22.7 (2009), p. 4.
[49] 李宗荣, 谢涵, and 徐碧波. “Informational Psychology Based on Theoretical Informatics”. In: 心理学进展 (2016). In Chinese.
[50] 李宗荣 and 马利奥·邦格. “论信息科学的世界观(V/V)”. In: 医学信息 11 (2008), pp. 5–27.
[51] 李宗荣 and 马里奥·邦格. “论信息科学的世界观”. In: 医学信息 12.8 (2008), pp. 2123–2130.
[52] 邬焜. 信息哲学. In Chinese.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53] 钟义信. 信息的科学.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54] 钟义信. 信息科学原理. 北京: 邮电大学出版社, 1996.